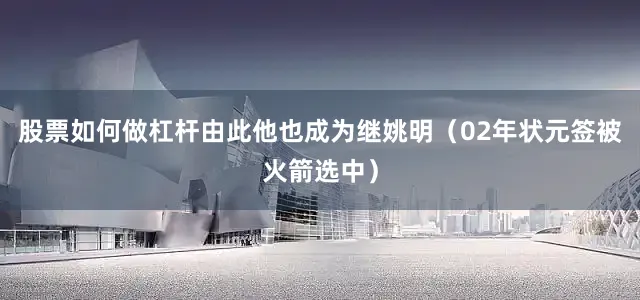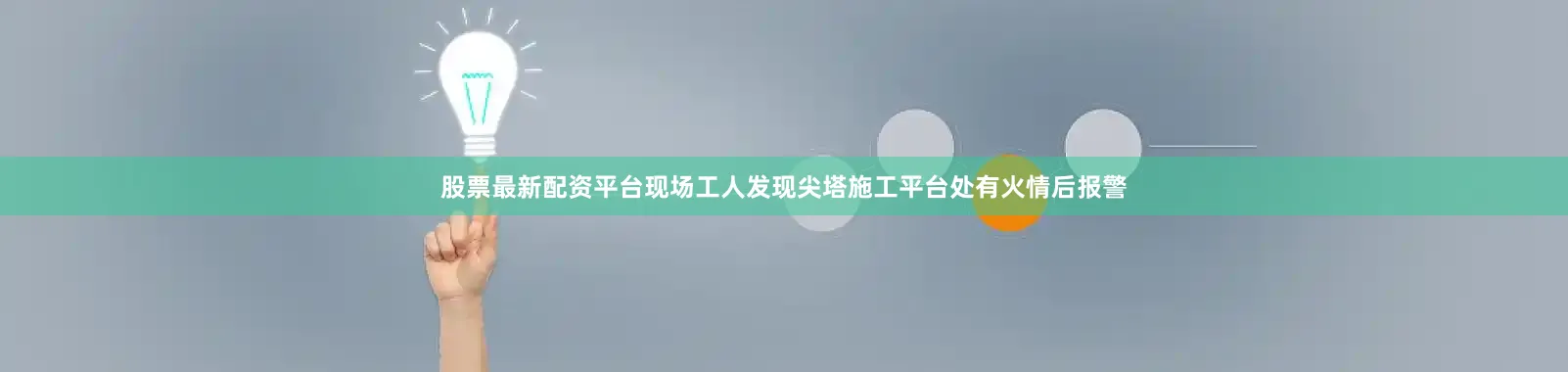你问现在的孩子 “虱子” 是啥,他们多半以为是某种动画片里的怪兽。可搁七八十年前,这玩意儿是真・国民级 “宠物”—— 没人主动养,但人人身上都少不了。上岁数的人回忆起那会儿,总说 “一到晚上脱衣服,灯底下能看见虱子在布纹里跑,跟赶集似的”。可奇怪的是,这曾经嚣张到 “人人喊打” 的小东西,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没了?今儿个咱就掰开揉碎了,聊聊虱子的 “黄金时代” 和它们的 “集体失踪案”。
一、虱子的 “鼎盛王朝”:那会儿人人都是 “饲养员”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要是谁身上没虱子,那才叫稀罕事。我奶奶总说,她年轻时带孩子,哄睡全靠 “逮虱子”—— 油灯底下,一手攥着孩子头发,一手拿篦子梳,“噼里啪啦” 掉下来的虱卵(那会儿叫 “虮子”)能接小半碗。梳下来的活虱子不能扔,捏死了血溅一手,她就往火塘里一丢,听着 “滋啦” 一声响,才算解气。
展开剩余90%这些芝麻大小的灰黑色虫子,其实是个 “大家族”,分工明确得很:
头虱是 “留守儿童”,专在头皮上扎根,孩子在学校里追跑打闹,头一蹭就从这个脑袋 “移民” 到那个脑袋。我爸说他上小学时,男生之间比谁头上的 “虮子” 多,把头发一撸,白花花的卵粘在发根上,跟撒了把小米似的,现在想起来还浑身痒。 体虱是 “居家宅男”,躲在衣缝、被褥里,尤其爱往棉袄的棉花缝里钻,天冷穿得多,它们就在腋下、腰腹这些暖和地方 “开饭”,咬得人一挠一个红点子,连成片能痒到睡不着。 ** 阴虱是 “私密访客”,靠亲密接触传播,那会儿卫生条件差,共用澡盆、混穿裤子,都可能让它们 “串门”。这些小吸血鬼的繁殖能力,简直能让养猪专业户都自愧不如。雌虱一天能下 6 到 8 个卵,跟小芝麻似的,外面裹着层黏糊糊的 “胶水”,牢牢粘在头发丝或衣服纤维上,拿水冲都冲不掉。七八天功夫,卵就孵出小虱子,再过半个月又能当爹妈,不出一个月,就能从 “一家三口” 发展成 “百八十口” 的大家族。
那时候灭虱,全靠土办法硬刚。农村妇女的标配是 “篦子 + 煤油”:篦子齿密得跟渔网似的,梳头时能把藏在发根的虱卵刮下来;煤油味儿大,能熏得虱子晕头转向,就是梳完头跟个 “行走的煤油灯” 似的,出门能把蚊子都熏倒。更绝的是煮衣服 —— 大铁锅里烧开水,把棉袄棉裤扔进去咕嘟咕嘟煮,捞出来晾的时候,布缝里能看到一层死虱子,跟撒了把黑胡椒面。
但这些办法都治标不治本。我爷爷说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干活,冬天一件棉袄穿俩月,晚上脱下来能抖出几十只活虱子,“咬得浑身痒,只能拿墙角蹭,蹭得棉袄都发亮”。还有人急了用 “六六粉”—— 那时候这农药管得不严,有人直接往头皮上抹,结果虱子没彻底死绝,人先头晕恶心,差点送了命。
二、为啥虱子那会儿这么 “嚣张”?日子糙是根源
现在想想,虱子能在那会儿 “横行霸道”,说到底还是因为日子过得太 “将就”。就跟现在的蟑螂喜欢脏乱差的厨房一样,那会儿的环境,简直是虱子的 “五星级度假村”。
首先是洗澡太奢侈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别说农村,连城里的工人家庭洗澡都得 “看天看粮”。我老家在华北平原,村里的井离得远,挑一担水得走二里地,夏天还好,冬天井水冰得刺骨,烧热一锅水得烧半捆柴火 —— 那时候柴火金贵,谁家舍得天天烧水洗澡?我奶奶说,冬天全家一个月能烧次热水擦身就不错了,“身上的泥垢能搓成条,虱子在里头钻着跟住山洞似的”。
城里稍好点,但也没方便到哪去。我姑姑 60 年代在纺织厂上班,厂里的澡堂子一周开两次,每次限时半小时,“进去跟下饺子似的,水龙头不够用,能冲个脊背就不错了”。赶上加班或阴雨天,一个月不洗澡是常事,“下班回来往床上一躺,虱子就从衣领里爬出来‘开饭’,痒得直哼哼也懒得动”。
其次是衣服太金贵,洗得太潦草。那会儿一件衣服往往 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孩子穿哥哥姐姐的旧衣,补丁摞补丁,布缝里藏的虱子卵根本洗不干净。更关键的是洗涤用品跟不上 —— 肥皂在那会儿是 “硬通货”,过年走亲戚拿两块肥皂当礼物都倍儿有面子。我妈说她小时候,家里的肥皂得切成小块用,“洗袜子都只敢蘸点沫子,哪敢使劲搓”。
这种肥皂去污力也差,只能洗掉表面的浮灰,对付虱子卵那层黏糊糊的 “胶水” 根本没用。1970 年代国产洗衣粉开始普及,但成分单一,顶多能去去油渍,洗棉袄时连布纹里的汗渍都搓不掉,更别说藏在里头的虱子卵了。我姥姥回忆说,那时候洗被子得用木槌在河边砸,“砸得胳膊酸,晒干了照样能找出虱卵,跟小芝麻似的粘在被单上”。
再就是居住环境太拥挤。那会儿一家五六个孩子是常态,农村土炕小,七八口人挤着睡,晚上谁身上的虱子爬出来,一晚上就能传遍全家。城里工人住 “筒子楼”,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三代人,衣服晾在公共走廊,孩子在楼道里疯跑,头碰头、衣挨衣,虱子 “串门” 比走亲戚还方便。
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卫生观念跟不上。那会儿人觉得 “身上有虱子是正常的”,甚至有点 “谁的虱子多谁壮实” 的歪理。我爷爷说他小时候,村里孩子比谁头上的 “虮子” 多,“梳下来能装满小玻璃瓶,还互相换着玩”。学校老师也头疼,上课总有人挠头挠脖子,“讲课讲到一半,看见前排女生头发上爬着个虱子,也只能假装没看见 —— 总不能让全班停课逮虱子吧?”
那会儿的虱子传播链,简直无孔不入。孩子在村口玩 “老鹰捉小鸡”,头碰头的瞬间,头虱就完成了 “迁徙”;妇女在河边共用洗衣盆,衣缝里的虱卵顺水漂,下游人家的衣服一泡,就成了新的 “孵化基地”;甚至赶集时人挤人,谁的棉袄蹭到谁的袖口,体虱就能趁机 “跳槽”。用我奶奶的话说:“那时候的虱子,比现在的微信传播还快,三天能传遍半个村。”
三、虱子的 “滑铁卢”:三大战役打跑了 “吸血军团”
虱子的好日子,大概持续到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这不是突然发生的,而是一场 “人民战争” 加上 “科技进步”,硬生生把这 “国民室友” 给赶跑了。
第一战:学校成了 “灭虱主战场”
上世纪 70 年代末,学校开始狠抓 “个人卫生”,每周一上午的 “卫生课”,其实就是 “灭虱大会”。老师拿着篦子挨个检查头发,谁头皮上有白花花的虱卵,立刻被拉到教室后排 “特殊处理”—— 要么叫家长来领回去洗头,要么让校医拿酒精棉擦头皮。
我表姐 1982 年上小学,她说那时候女生必须剪短发,“老师说长发容易藏虱子,谁留辫子就天天被盯着梳”。男生更惨,头发被推成 “板寸”,头皮都能看见,虱子想藏都没地方去。学校还发防虱宣传画,画着虱子怎么传播、怎么消灭,虽然画得粗糙,但比家长唠叨管用多了。
家里也跟着学校 “同步行动”。我姑姑那时候给表姐梳头,用篦子梳完,还得拿白酒泡头皮 —— 白酒能杀死虱子,但味儿冲,表姐说她上课总被同学笑 “一股酒气”。周末全家 “大清洗”,棉袄棉裤拆下来,用开水烫、用肥皂搓,我姑父负责烧火,我姑姑负责捶打,“泡沫里漂着死虱子,跟下小雨似的”。
第二战:化学武器登场,虱子扛不住了
真正让虱子 “元气大伤” 的,是 1980 年代后出现的 “化学灭虱神器”。最早是含 “敌百虫” 的洗头膏,虽然有点毒性,但对付头虱效果奇好 —— 抹在头皮上捂十分钟,虱子就蜷成一团死了,虱卵也能被软化,用篦子一梳就掉。
我妈说她 1985 年在供销社买过这种洗头膏,“一块五一小瓶,舍不得用,专门给孩子洗头时用”。后来更安全的 “氯菊酯” 类药剂出现,医院和防疫站开始免费发放灭虱药膏,医生挨家挨户教用法:“抹在头发上别洗掉,戴个浴帽捂一夜,第二天虱子全死光。”
体虱也遇到了克星 ——1980 年代中期,含 “除菌成分” 的洗衣粉开始普及。这种洗衣粉比老式肥皂厉害多了,泡衣服时能渗透到布纹里,把藏在衣缝的虱子卵都泡软,搓洗时一使劲就掉。我姥姥第一次用这种洗衣粉,洗完被子晒干后,翻来覆去找不到一只虱子,“当时还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了,摸了好几遍才敢相信”。
第三战:日子过好了,虱子没了 “生存土壤”
说到底,灭虱最关键的武器,还是 “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”。1990 年代后,虱子的 “生存空间” 被一点点挤压,直到最后没了立足之地。
先说说洗澡这件事。1980 年代末,城里单元楼开始装热水器,虽然是耗电的 “电热水器”,但拧开就能出热水,不用再烧柴火、挑水了。我家 1992 年搬进楼房,我爸说 “第一次天天洗澡,身上搓下来的泥能吓坏个人,洗了一个月,突然发现晚上睡觉不痒痒了 —— 虱子早就被冲没了”。
农村虽然慢点,但变化也大。2000 年后,国家搞 “农村安全饮水工程”,村里接上了自来水,压水井也普及了,挑水不再是难事。冬天虽然冷,但太阳能热水器进了农家,晒一天就能有温水擦身,“一个月洗一次澡” 成了老黄历。我老家堂哥说,2010 年他家装了太阳能,“我爹 70 多岁,现在三天洗一次澡,说‘身上清爽,睡觉都香’”。
衣服也不再 “新三年旧三年” 了。1990 年代后,化纤衣服普及,这种料子光滑,虱子不容易附着,而且洗起来方便,扔进洗衣机转半小时,比手搓得干净多了。农村姑娘也开始穿 “的确良” 衬衫,城里人更是一季买好几身衣服,“换得勤了,虱子还没来得及繁殖,就被洗掉了”。
居住环境的改善更致命。农村土炕换成了木板床,铺的是光滑的床单被罩,每周能拆下来洗一次;城里楼房有独立卫生间,衣服晾在自家阳台,再也不会跟邻居的衣服 “串门”。虱子没了拥挤的 “集体宿舍”,也没了互相 “串门” 的机会,想繁殖都难。
四、虱子的 “余波”:它们真的彻底消失了吗?
现在你要是在身上发现个虫子,大概率是蚊子或蟑螂,想找只虱子比找野生东北虎还难。但这小东西并没完全灭绝,只是 “退居幕后” 了。
比如欧美国家,因为人喜欢留长发、体毛旺盛,头虱偶尔还会在学校爆发。新闻里总说 “某小学出现头虱,家长紧急给孩子剃光头”。还有流浪汉收容所、战乱地区,卫生条件差的时候,体虱也会卷土重来,甚至可能传播斑疹伤寒等疾病。
国内也不是完全没有。疾控中心的朋友说,偶尔会接到幼儿园的报告,说几个孩子头上发现头虱,“多半是共用帽子、枕头,或者玩的时候贴太近传染的”。但这种情况很少见,只要及时用灭虱药,很快就能控制住,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“全家沦陷” 了。
专家也提醒,现在想预防虱子,其实很简单:孩子别跟人共用帽子、梳子;去公共场所别随便躺卧;回家后及时换衣服、洗头。真发现头上有小虫子在爬,别慌 —— 药店买瓶含 “氯菊酯” 的洗头膏,按说明用两次,基本就能搞定,比当年的煤油、六六粉安全多了。
五、虱子退场,藏着日子变好的密码
虱子的消失,看似是个小生物的兴衰史,其实藏着咱老百姓生活变好的大故事。从 “人人身上有虱子” 到 “见不到一只虱子”,这背后是洗澡从 “奢侈事” 变成 “日常事”,是衣服从 “缝缝补补” 变成 “常换常新”,是卫生观念从 “无所谓” 变成 “很重要”。
上世纪 50 年代,人最关心的是 “能不能吃饱”,洗澡、换衣服这些 “小事” 根本顾不上;1970 年代,工分和粮票是生活重心,能有块肥皂就算 “讲究人”;1990 年代后,日子宽裕了,超市里沐浴露、洗发水摆得满满当当,洗衣机成了家家必备的家电,冬天洗澡再也不用烧柴火,衣服脏了随时能洗 —— 虱子没了生存的 “土壤”,自然就消失了。
2003 年 “非典” 后,国家更重视公共卫生,学校、社区、农村都开始搞 “爱国卫生运动”,垃圾桶分类了,公共厕所消毒了,连农村都通了自来水、建了沼气池,卫生条件跟以前比,简直是天上地下。我爷爷今年 88 岁,每次看家里的热水器和洗衣机,总念叨:“以前哪敢想啊,现在洗澡跟喝水一样方便,虱子想活都难。”
现在偶尔听老人聊起虱子,年轻人总觉得像天方夜谭。但对那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,虱子的记忆里藏着太多故事 —— 有油灯下母女逮虱子的温情,有冬天洗冷水澡的酸爽,有第一次用洗发水的新奇。这些故事和挑水的扁担、补丁摞补丁的棉袄、挤得翻身都难的土炕一起,成了老相册里的泛黄影像。
虱子的集体失踪,其实是件挺让人感慨的事。它像个隐形的标尺,悄悄丈量着日子的变化。当我们再也不用为身上的虱子发愁时,其实是在享受着时代进步带来的 “小确幸”—— 这种 “不痒痒” 的自由,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说明:咱的日子,是真的越过越舒坦了。
发布于:江西省领航配资-炒股配资皆-正规线上配资-配资公司排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散户炒股如何加杠杆活动主页上显示:大牌1.9元起
- 下一篇:没有了